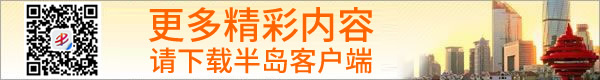时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的荣学证获得了“抗击非典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并荣立省三等功。
“消毒药物的品种较多,如来苏水 、过氧乙酸、巴氏消毒液、醛类等。此外,请别忘了阳光,它是最好的消毒剂。”这是2003年时一份抗非典常识小资料中的一句话。它的最后一句耐人寻味。“阳光”是消毒剂,对某些病毒是这样 ,对因疾病、变故、流言造成的恐慌也是这样。经历抗击非典一役,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律法开始提速,新闻发言人制度得到推广。借着那个契机,从中央到地方都做出了很多改变。也正是在那个时候,青岛成为山东省第一个设立新闻发言人的城市。
非典来临时的恐慌 “要不是你来采访,非典的事还真很少去想。”李善鹏见到记者,这样说道。现在,他是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彼时,他是青岛市防治非典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曾亲身经历发生在青岛的“非典之战”。
2003年4月,整个青岛都陷入了恐惧的慌乱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大家知道的只有一点:尽量少出门,尽量带口罩。
在城市的主要交通入口,常常可以看到排队检查的车流。除了要测体温,还要逐个登记。医院专门设立了发热门诊,发现了一个人体温偏高,会马上进行隔离观察。即使是侦破刑事案件,抓到嫌疑人也先要查体温。
由于需要大量的体温计,全市体温计不够用,还曾动员党政干部捐体温计。
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荣学证刚工作没几天,市九州体育部门的一份书面报告就放到了他的桌上:建议对与外界接触最多的列车乘务人员集中隔离。
有市民发现原来闲置的东部别墅晚上有了灯光,便强烈要求对别墅区进行拉网式搜查,并要求严令各单位不许邀请、接待北京来人。
某区的指挥部还曾发过一个后来被纠正的通告:凡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立呼吸道发热门诊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一律不准私自留治发热、咳嗽病人。
很多村民自发地把村口的路截断,不准外来车辆进村。
堵和逃,是面对未知恐惧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早在2002年12月,广东就已出现了非典患者,但当时,官方的选择是:严密控制信息,禁止媒体报道。与此同时,小道消息和谣言借助网络、短信等方式漫天飞扬。广东出现了抢购白醋、板蓝根等用品的热潮 。
直到2003年2月11日 ,人民网上才出现最早有关“非典型肺炎”的报道:《广州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
虽然有了相关报道,但官方的态度一直是“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媒体的报道也是以正面宣传为主。当时,在疫情较为严重的北京,人们仍被告知:“北京是安全的”。
疫情公开带来平静 情况在2003年4月20日迎来转机。当天,张文康被免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职务,孟学农被免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同一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关于非典疫情的新闻发布会表示,北京疫情已经很严重,非典有漏报问题。截至4月18日 ,北京已确诊非典患者339例,这个数字是前四天公布的数字“37例患者”的近10倍。自此之后,信息的闸门才一下被打开,各种报道山呼海啸般涌来。
事实上,早在2003年2月,李善鹏就已经从网络上知道了广东有这么一种“很厉害的非典型肺炎”。但当时,包括青岛在内的全国各地卫生防疫部门都没有采取应对措施,就这么一直观察着,直到四月,调查疫情、信息公开的决策才随着中央的步调全面展开来。
青岛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例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钱某,非典期间,他的妻子和多位家人相继感染并死亡,4月23日 ,钱某经妻子苦苦劝说,带儿子悄悄潜回青岛,两天后钱某出现发热症状。26日,他主动打“120”电话求救,被接送到市胸科医院发热门诊并当即留院。
当时的青岛市防治“非典”专家组组长秦筱梅告诉记者,对于是否上报为非典疑似病例,各方犹豫不定。直到5月8日公布疑似病例的那天早上,指挥部还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一事情。而此时,岛城早已人心惶惶,各种谣言猜测纷起。最终指挥部的领导一致决定坚持上报,并力主青岛市与省里同步向社会公开。
当天,指挥部就举行了新闻通报会,真实详细地向社会公布了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例的有关情况。随后,又对群众通过网络和热线电话等反映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有针对性地撰写稿件,解疑释惑,消除了群众的猜疑和不满。群众的情绪日趋平静。
信息公开成“非典遗产” “谣言止于公开。”在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现代传播研究所所长杨善民看来,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最好办法还是公开透明。“只有公开、透明,以清晰信息克制模糊信息,才能控制谣言,夺取舆论主导权。”
2003年“非典”引发了社会普遍的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的关注,尽快建立健全在公民知情权基础上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成为人们的共识。
“正是那场‘非典’风波,暴露出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严重滞后的不足,也使公众对政务信息公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杨善民告诉记者,从那以后,立法速度大大加快了。
在非典爆发后的几个月里,广州市率先出台了《政府政务信息公开法》,及至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公民的知情权第一次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保障。
在杨善民的眼里,非典蔓延的2003年还是我国新闻发布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年。“如果说这之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被动起步的话,从抗击非典之后就开始了主动性的发展。”
非典结束后的当年9月22日,国新办在北京顺义举办了后来被称为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的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培养出了的学员,包括了后来的九州体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和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
当然,青岛也没有落后。2003年5月,便紧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步伐 ,确定了在各区市及政府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成为我省第一个设立新闻发言人的城市。
非典的“遗产”不止于此。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青岛市危机管理专家组成员郑敬高看来,在非典之前,中国的各级政府是没有任何危机管理意识的。以至于灾难来临的时候,手忙脚乱,并出了很多问题。
非典之后,政府开始设立应急办等相关部门,开始重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
2006年,青岛市应急办成立。现在,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已经有了三十多份应急预案,基本涵盖了公共突发事件的各个方面。
在《青岛市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预案》里就规定了,如果是一级响应,市应急指挥部可以提出停课、关闭公共场所等建议以及新闻媒体24小时播放相关防治知识宣传等措施。
青岛市应急办副主任杨茂文告诉记者,如果再发生类似非典这样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办就会按照相关预案的要求,协调各个部门,开展各项应急工作。
卫生防疫事业的转机 “当时也没想到,SARS会这么厉害。”李善鹏说,如果现在再有这样的疫情,疾控中心肯定第一时间要进行防堵,“御疫情于市门之外”。
这种情况在2010年防控甲流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甲流开始发现于国外,虽然我国还没有,但我们已经启动了相关的防控措施。”
在非典时,确诊病例还是省级以上部门的权力。后经过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到甲流时,青岛就已经有确诊病例的权力了。
在非典之后,我国启动了卫生防疫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此前被广泛诟病的诸多法律漏洞相继被补上。
在非典爆发当年的5月7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就被紧急制定出来,并在国务院第7次常务会议上通过。此后,我国又修改了《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和《动物防疫法》等诸多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在后来的甲流防治中,作用开始显现。
比如,甲流疫情发生不久,即迅速被宣布为乙类传染病,甲类处理。
在李善鹏看来,非典之后,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得到了迅速地发展。现在,如果中国的某个地方再有类似SARS这样的疫情,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当天就会上传到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中,各级卫生部门当天就可以得到讯息,布置防控 。“这在非典之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李善鹏说,这就是非典这场灾难带给我们的反思和改变。
文/图
记者 周超 (来源:九州体育-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