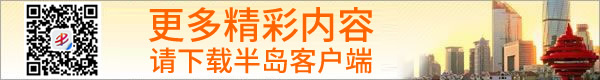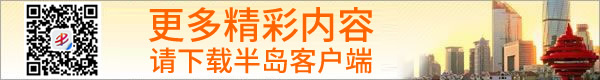如果把新闻比做女人,至少有两种:骨感的和肉感的,虽然报社的女记者大都奔波得很骨感,但希望奉献给读者的新闻都是鲜活的,有肉的。
跟春晚“死磕”
文艺部 王法艳
没什么文化的人都喜欢在文章开头提一下自己最近看了什么书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星期一是礼拜几》,写的是某著名杂志社一菜鸟记者荒诞、狼狈的记者生涯。我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写得很幽默,对媒体生态的描述也很真实,让我不时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5年修炼成“绕指柔”
作为一名文娱记者,虽然也会关注一些严肃的文化现象和深度的产业话题,但大多数时候,我负责提供给读者的新闻是轻松的、娱乐的,主任经常耳提面命的是:“稿子写得有趣点。”稿子读着好玩,但稿子“出炉”的过程往往就没那么好玩了。5年前初做娱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座右铭都是“脸皮可以厚一点”,大牌身边的“小鬼”难缠,小明星更要摆足架子以壮声势,直至把原本脆弱抓狂的本娱记修炼成淡定的“绕指柔”。我曾在大雨中打着一把塑料伞在上海大剧院门口比戴望舒笔下的女郎还要哀怨地站了两个多小时,只为能采到莎朗·斯通;也曾在凌晨三点接到一位屡放我鸽子的明星电话说“现在过来采吧”,迷迷瞪瞪中闹不明白这是个好消息还是个坏消息。
明星难采,但最难采的是央视春晚,而这也是一年到头中最受关注的娱乐事件。但春晚剧组为了保证节目的神秘性和惊艳感,每次彩排都是“防火防记者”,娱记们想得到点关于春晚的消息,要么就得潜伏到内部,要么就得“策反”某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士。
第一次“混”春晚
我第一次采访春晚,是在2008年年初,那时候还不知道可以在带观众彩排时花高价从观众手中买观摩票。每天在嗖嗖的冷风里,围着央视大楼徘徊又徘徊,不得其门而入。后来,同事张文艳的一位在央视工作的同学,愿意把我带进大楼,但能不能混进彩排演播大厅,还得靠运气。该同学千叮咛万嘱咐,千万潜伏好别暴露了,要不一查监控录像就知道他是“内鬼”了。
连过三道关卡,终于来到演播厅外面,观察了一下地形,演播厅的每个入口都有两名保安把守,走廊里还有很多保安在流动“抓捕”可疑分子,据说前一天就有好几个记者不幸“落网”。二楼还有穿西装戴白色手套的便衣居高临下掌控全局。我只好很低调地坐在一张椅子上,切身感受到了当年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生存环境之恶劣。表面上按兵不动实则内心焦灼万分,眼看着一点点接近彩排时间了,可还是毫无办法突破最后的防线。
内心正在翻江倒海之际,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位同行送给一位已高升到广电总局的前领导两盒西湖龙井,得到了一张观摩票。她打算进去后让别人再把票带给我,看我能不能以“出来上洗手间了”为由混进去,后来发现此法不通,保安要求观众从同一个门进出,这样保安不仅认票还认人,双保险,我那点刚刚燃起的希望小火苗,又扑哧一声被浇灭了。
但有句古话叫“天无绝人之路”,还有句古诗叫“柳暗花明又一村”,挨着那位同行就坐的一位美女居然有两张票,她很慷慨地将其中一张票给了我。拿到票,我俨然是偷渡客拿到了绿卡,美滋滋但佯装镇定地进入了传说中的央视一号演播大厅。不过潜伏没有就此结束,大厅内还有很多巡视人员,我脱下羽绒服盖着笔记本和握笔的手,边看节目边不动声色地“盲记”,在彩排进入尾声唱响《难忘今宵》的时候,又赶紧趁乱拿出相机拍了两张照片。那天走出央视大楼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我第一次发现夜幕下的北京如此迷人。
“磨"进阅兵村
时政新闻部 孟琳达
从报社一茬茬的新面孔上,总能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很幸运,从转正那天起,我成了时政新闻部的一员,其中跑党政和部队口的经历让我收获颇丰。这期间,60年“一遇”的国庆大阅兵,是我至今最最宝贵的财富,记者这行的酸甜苦辣,对我来讲,那一个月体会得最深。
“恶劣”环境,寻找突破口
2009年9月6日凌晨,我和两名同事被“空投”到了北京,采访10月1日的国庆大阅兵。完全陌生的环境 ,一切从零开始。
9月初,阅兵新闻环境“很恶劣”,很多“阅兵”消息都处在保密阶段 。3个人来京,总不能天天去“扫街”,如何能零距离接近阅兵方队、亲自进入阅兵村 ,成为我每天琢磨的问题。
阅兵村一共有三个,一般村内外共有四道警戒线:第一道由北京公安部门承担、第二道由预备役部队承担、第三道由空军地勤部队承担、第四道由北京卫戎区部队承担。另外,天上有直升机大队昼夜执勤,四道警戒线和直升机大队组成了一个无形的大网,外人想进入必须层层申报,连中央级媒体想进阅兵村都千难万难。
当时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所有能帮助到我的朋友找线索打电话。“除非有‘捷径’,否则进村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当时很多同行说得最多的话。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进京的第4天,通过某舰队的朋友,要到了负责阅兵村采访事宜的海军军区某领导的电话,“电话给你,人家愿不愿意帮你,你能不能进村 ,靠运气了!”电话那头,朋友如是说。
沟通的日子相当艰难,记得第一次给军区领导打电话时,人家一听是地方媒体,听完介绍后就礼貌地挂断了电话,随后发的短信,就像石沉大海,很难得到回复。即便在(海军大院)门口苦等几小时,也难见领导一面。几天之后,终于收到回复:“带上资料来海军大院。”沟通的结果是,决定破例带我进三村中最“神秘”的装备阅兵村进行探访。前提是——不能写稿、全程保密。
不放弃,最终收获发稿权
进村那天是9月11日,我有幸在“仿造天安门前”提前目睹了装备方队、空军方阵气势的联合汇演,也采访到了很多一手的资料。但由于新闻纪律的限制,最终见报的信息少之又少。可不让发稿传照片,千辛万苦进入阅兵村实地采访的机会不就浪费了吗?为了能取得受阅部队领导的信任,争取发稿权,参观期间我一刻不停地在有限区域内尽可能地搜集新闻点,然后把新闻点一条条列在采访本上,一有机会就逮住部队领导“审稿”,不让提的我坚决“删除”,就这样,几十条新闻最终被删到仅剩三四条了。最终,在临出村的前10分钟,我握着手中的4条线索,争取到了发稿权,并获得了领导的批准签字,同时获批的还有我偷偷用卡片机拍下来的部分照片。
9月11日采写的一篇《连过四道关,记者首进阅兵村》的稿件,让本报成为全国首家进入神秘阅兵村采访的地方媒体。随后,我又辗转和北京武警总队的领导取得了联系,并有了固定的通讯员,能在第一时间和北京媒体同步报道各类阅兵故事。
“不放弃,不到万念俱灰永远都不可以放弃。”“你是记者,怎么能拿‘采访不到’当理由?”这两句话是曾带过我的一位领导教给我的。3年的采访经历让我明白,作为记者,外表柔弱也可以做到内心强大。
(来源:九州体育-半岛都市报) [编辑: 王好]
版权稿件,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